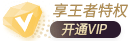-9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3 期(民國 98 年 3 月),97-145
©中 央 研 究 院近 代 史 研究 所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王宏志 **
摘 要
儘管不少中西學者對馬戛爾尼訪華作過研究,但長久以來仍然忽略
了一個重要元素:翻譯在這次中英第一次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透
過對原始資料的疏理,以及中英兩國文件的文本對比,除整理和分析當
時中英雙方的譯者背景及翻譯活動外,更論證譯者對重要文件的改動構
成了嚴重的溝通問題,甚至是馬戛爾尼被乾隆視為貢使的重要因素,也
是馬戛爾尼無法完成任務的主要原因。然而,本文亦指出,這責任不在
譯者,他們的翻譯是在中英不同的政治及外交文化的制約下運作的。種
種的改動,儘管產生嚴重的後果,但也是無可避免的了。
關鍵詞:馬戛爾尼使團、翻譯研究、朝貢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收稿日期:2008 年 9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年 2 月 6 日。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教授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98-
該國遣使入貢,安得謂之欽差。
此不過該通事仿效天朝稱呼,
自尊其使臣之詞。1
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勳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使團到中國,攜帶豐盛的禮物,以補祝賀乾隆八十大壽為名,
嘗試打開中國的大門,爭取較好的商業條件,甚至希望能在中國設置使館,割
讓或租借港口。2不過,這次中英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觸卻多被視為徹底失敗,
馬戛爾尼只能短暫地跟乾隆見過兩次面後便被指示離開,並沒有達到原來設定
的任何目標。
關於這次中英外交史上重要的開端,3原始資料頗為充裕,4為有關研究提
1 〈諭軍機大臣著梁肯堂筵宴後仍回河工並飭知委員不得稱貢使為欽差〉,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以下簡稱
《史料滙編》),頁 40。
2 有關東印度公司對馬戛爾尼所發出的指示及馬戛爾尼所作的報告,見 Earl H. Pritchard, ed.,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 1792-4,” in Patrick Tuck (select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Vol. VII, pp. 201-509.
3 早在 1583 年(明萬曆十一年)及 1596 年(萬曆二十四年),英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曾兩度致書中國皇帝,試圖跟中國開展貿易,但估計送信船隻在途中遇險,中國方
面看來並沒有接到英人入朝的消息。參見張軼東,〈中英兩國最早的接觸〉,《歷史研究》,
1958 年第 5 期,頁 31-32;兩信的中譯,見同文附錄一及二,頁 42-43。此外,在派遣馬戛爾尼
來華前,英國政府曾在 1787 年(乾隆五十二年)組成訪華使團,由加茨喀特(Lt. Col. Charles
Cathcart)率領,12 月 21 日自英國港口斯庇漢(Spithead)出發,但在使團抵達蘇門答臘附近的班
卡海峽(Straits of Banka)時,加茨喀特在 1788 年 6 月 10 日病逝,使團被迫折回。有關加茨喀特
使團,可參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以下簡稱 The Chronicles),Vol. I, pp. 151-171;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以下簡稱 The Crucial Years), pp. 236-271.
4 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著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詳細開列了中西方的原始資料,參見 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 (Jon Rothschile Tr., London: Harvill, 1993)
(以下簡稱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pp. 597-602. 不過,今天較容易見到的,除註 2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99-
供很大的方便。事實上,過去有不少史學家曾作過深入研究,從不同角度去探
討使團失敗的原因。在過去,主流論述認為,清廷錯誤地把這些國際間互訪的
正常外交活動視為蠻夷藩屬要到中華帝國朝貢的舉措,導致使團失敗而回,而
覲見乾隆時的叩拜禮儀問題被認定為最關鍵的因素。5大部份歷史家批評乾隆
堅守閉關政策,以保護主義拒絕與西方接軌,愚昧地放棄了中國走向近代化的
機會,這甚至被視為導致後來中英鴉片戰爭的遠因。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
見,認為這次中英相遇是兩個不同文化觀念的帝國一次正面交鋒和衝突,乾隆
拒絕英國人的貿易要求並不是出於頑固、保守或封閉的心態,而是因為其他經
濟及政治方面的考慮,6更有人強調乾隆並不是閉關自守的君主;他拒絕馬戛
爾尼的要求,其實是「洞悉其奸」,看破馬戛爾尼來華的政治陰謀。7
所列東印度公司對馬戛爾尼所發出的指示和馬戛爾尼所作的報告外,使團大使馬戛爾尼及副使
斯 當 東 (Sir George L. Staunton, 1737-1801) 都 對 這 次 出 使 作 了 詳 細 的 日 誌 紀 錄 :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in Patrick Tuck (select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以下簡稱 An Embassy to China), Vol.
VIII, pp. 61-220;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以下簡稱 An Authentic
Account);另外,當時在北京的天主教士曾寫過一些書信,也是很重要的原始資料。參見 Earl
H.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Vol. XXXI (1934), pp. 1-57。又據黃一農指出,大型資料庫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http://www.gale.com/EighteenthCentury/)中收有約 20 種與馬戛爾尼使團相關的專書。參見黃一
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1 分(2007),頁 41,註 23。中文原始材料方面,可參見〈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收入
故宮(北京)博物院文獻館編,《掌故叢編》(台北:國風出版社,1964),頁 46-86。不過,
最齊備的是上開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史料滙編》。
5 由於中英雙方的當事人對這問題存有不同的論述,究竟馬戛爾尼有沒有對乾隆行三跪九叩禮,
學界至今仍然沒有定論。近年最細緻的論述見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
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1 分,頁 35-106。
6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下簡稱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7 趙剛,〈是什麼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 世紀世界視野中的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事件〉,收入
李陀、陳燕谷主編,《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 9 輯,頁 2-28。各種
不同的論述和觀點也反映在一次為紀念這次通使 200 周年而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中。
參見張芝聯主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另外,英國漢學研究會在 1992 年也舉辦了一次國際研究會,紀念馬戛爾尼訪華二百周年,部份
論文出版為: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0-
本文不打算進一步分析或判定這次中英交鋒的性質,更不想在叩拜禮儀問
題上再作糾纏,而是希望能夠處理一個長期以來被忽略的元素:翻譯。8
本來,國際間外交活動須得倚賴翻譯,是非常淺顯的道理。可是,由於中
英兩國在馬戛爾尼使團以前從來沒有過任何正式的外交往來,而清廷一向嚴格
限制外國人學習中文,中國人本身也從來沒有學習外語的意願,根本沒法找到
合資格和具備水平的譯者,加上當時兩國政治、文化和語言模式的差異,使這
次外交活動的翻譯問題變得極其複雜。事實上,從下文的分析可以見到,缺乏
合格的譯者和翻譯,甚至是這次使團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深入探討英
使團來華期間中英雙方的翻譯活動,對於我們理解這次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
件,會有莫大的幫助。
二
作為壟斷在華貿易的英國商務機構,東印度公司長期以來都面對著如何處
理中英語言溝通障礙的問題。據說,早在 1617 年 1 月,英王占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便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中國皇帝〔時為明神宗萬曆年間(1563-1602)],
提出要拓展中英商務,但是當信送到中國後,卻沒有能夠找到中國人願意協助
把信件譯成中文,也沒有人膽敢傳遞信件,因為那是會被判死刑的罪行。9事實
上,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發生的「洪任輝事件」裏,10乾隆便明確下諭「內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3).
8 直至最近,我們才見到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翻譯問題的討論:季壓西、陳偉民,〈馬戛爾尼使
華(1792-1793):中英早期交往中的語言障礙〉,《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頁 1-48。這算是一個開端。不過,該書在資料方面很受限制,只參考了中國大陸已出版的材料
(全文大量引用馬戛爾尼和斯當東回憶錄的中譯本),西方的資料完全闕如,且在論述上也只
是平舖直敍地羅列資料,較少見到自己的論述和見解。
9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 p. 10.
10 洪任輝原名為 James Flint,早年在廣州任職於東印度公司,並學習漢語。乾隆二十二年(1757),
清政府宣布限令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東印度公司派遣洪任輝乘船到天津呈訴,一方面控告粵海
關勒索,另一方面要求寧波開埠,但清廷採取強硬手段對應,除處死代寫狀文的劉亞匾、圈禁
洪任輝外,更於稍後制定《防範外夷規條》,加緊管控。關於洪任輝事件,原始資料見〈乾隆
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史料旬刊》,期 3,頁天 91 至天 95、期 4,頁天 113 至天 125、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01-
地人代寫呈詞者尤應嚴其處分」,11結果,代寫狀文的劉亞匾遭處決,就是洪
任輝(James Flint)也被判在澳門「圈禁三年」,然後驅逐回國。因此,在一段
很長的時間裏,中英間在廣州的溝通只能依賴朝廷所認可的一些所謂「通事」
來進行。
必須指出,這些通事絕大多數都沒有正式學習過英語。即使到了十九世
紀,當時住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仍說,
通事們除了自己的母語外,什麼別的語言也不懂;12此外,他又曾經詳細報導
過一樁審訊過程,涉及的是一名闖入福建水域的印度水手,裏面的首席通事「老
湯姆」13和他那原來是木工匠的助手怎樣以希奇古怪的手法來完成翻譯的工
作,正如亨特所說:那完全是一場「這樣好看的鬧劇」。14這些通事所掌握的
所謂「外語」,其實只是所謂的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那「毫無疑問是
中國人自己所發明的」,15是一種變形和扭曲了的廣州話與英語混合體,還滲
入了葡語、印度語、馬拉語,但卻「沒有句法、也沒有邏輯聯繫」,16一般英
國人是不會懂的。依靠這樣的通事來進行翻譯,情況的惡劣是可想而知了。在
東印度公司的文件裏,我們經常見到他們對於依靠這些通事來進行翻譯所產生
的種種問題和抱怨,這裏徵引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要透過行商把一封信忠實地翻譯出來,當中的困難幾乎是無法逾越
期 5,頁天 156 至天 162、期 6,頁天 198 至天 200 及期 9,頁天 304 至天 310;另可參見陳東
林、李丹慧,〈乾隆限令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任輝事件論〉,《歷史檔案》,1987 年第
1 期,頁 94-101;林健,〈洪任輝案─兼論乾隆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清史研究集》,
第 6 輯(1988),頁 265-279;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18 世紀的外交與中國命運》(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64-76。
11 〈新柱等奏現在遵旨查辦李永標摺〉,《史料旬刊》,期 4,天 118。
12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2), p. 50.
13 據考證,亨特筆下的首席通事「老湯姆」,即總通事蔡懋,當時辦有寬和通事館。參威廉‧C‧
亨特著,馮樹鐵譯,駱幼玲、章文欽校,《廣州「番鬼」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頁 37,註 3。
14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55), pp. 21-30.
15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p. 61.
16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p. 61.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2-
的。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只能夠大約領會其中的意思。17
除了語言能力外,通事的職業操守也受到質疑。在上面提過亨特所描述的審判
過程中,那位通事助手從頭到尾只管不停地向犯人推銷自己的商品,然後向官
員編造故事,亂說一通,根本沒有什麼職業操守可言。令問題變得更複雜的是,
通事和行商往往處於中國官員與外國商人的夾縫間,利益上的衝突嚴重地影響
翻譯的順利進行。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有這樣的觀察:
行商和通事不僅對廣州英語只有最基本的理解,而且他們的利益也跟公司
不一致。他們膽子也太小了,不敢準確地譯出官員們不想聽的話來。18
不過,儘管事實確是如此,也不能過於責怪這些通事,每當官員對外商有所不
滿時,通事和行商往往要負上刑責,遭到拘捕、拷打和責問。這是長久以來的
措施。19在這情形下,這些通事是沒法客觀和公正地完成翻譯工作的。
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職員便長期被迫接受這些水平低劣的通事,作為他們
跟中方官員溝通的橋樑。很明顯地,由馬戛爾尼所率領的正式官方外交使團,
不可能借助這樣的通事來協助翻譯工作。從最早的籌備階段開始,馬戛爾尼便
清楚明白到解決翻譯問題的重要性,在三十名文職人員中設立兩名翻譯官之
職。不過,要找得合適稱職的中英文翻譯官,在當時幾乎是無法解決的難題,
英國根本沒有這樣的人選。在馬戛爾尼以前所委派的加茨喀特(Lt. Col. Charles
Cathcart)使團,於尋找翻譯人員時已遇到很大的困難,儘管洪任輝當時已獲釋
回到英國去,但卻不准再到中國,最後他們找到一名曾在北京居住多年的法國
人 M. Galbert 充任翻譯。20不過,Galbert 在使團回程途中去世,21結果,馬戛
17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 7.
18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Vol. III, p. 31.
19 到了後來〔道光十五年(1835)],兩廣總督盧坤更以明文規定夷館內的看門、挑夫、看貨夫等,「其
人夫責成夷館買辦代僱,買辦責成通事保充,通事責成洋商保充,層遞箝制,如有勾串不法,惟代
僱、保充之人是問」。梁廷柟,《粵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卷 29,頁 565。
20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pp. 239, 247. 有關 M. Galbert 的材料很少,從普理查德的描
述,我們知道他在北京學習中文,後來在廣州任翻譯,曾參與 1784-1785 年 Lady Hughes 號鳴
放禮炮誤殺兩名中國官員的案件。
21 Earl H.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p. 262.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03-
爾尼只得委派他的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到歐洲大陸
去尋找翻譯人員,22斯當東在巴黎、歌德堡、歌本哈根及里斯本都找不到合適
人選,最後在意大利那不斯傳道會(De Propaganda Fide)所辦的一所華人書院
(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兩名剛完成傳道訓練的中國教士,名字分別叫周保羅
(Paolo Cho)及李雅各(Jacobus Li,又叫作 Jacob Ly,Plumb 先生),23能夠擔
任中文和意大利文及拉丁文的翻譯工作。24使團答應每人的工資 150 鎊,25這
是很高的報酬,足見他們對翻譯人員的重視。
有關這兩位翻譯人員的資料並不多,其中周保羅並不見於方豪所考證的道
光朝以前到歐洲留學的學生名單內。另一方面,李雅各漢名叫李自標,但在清
廷的文件裏,他的名字變成「婁門」,26這其實是“Plum”一個不太準確的音譯
─使團裏因為他姓李而為他取的叫法。李氏原籍甘肅武威,屬於少數民族,
乾隆二十五年(1760)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與另外 7 位中國年青人一起到歐
洲學習。27不過,無論是周保羅還是李雅各,他們都算不上是理想的翻譯人選,
因為他們都不懂英語,只能翻譯拉丁文。雖然馬戛爾尼自己諳熟拉丁文,但其
他隨團成員並不一定懂得拉丁文,因此,每次翻譯都得要輾轉進行,很不方便。
22 早從順治年間開始,西方傳教士已開始把一些中國人帶到歐洲去接受傳教的訓練。現在知道最
早的一位是 1650 年(順治七年)跟隨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P. Martin Martini)到歐洲的鄭瑪諾(又
名維信,西文名字為 Emmanuel de Sequeira),他在羅馬公學學習,1671 年(康熙十年)與閔
明我、恩理格等回到北京,1673 年(康熙十二年)逝世。此外,1707 年(康熙四十六年),山
西平陽人樊守義曾跟隨傳教士到歐洲,在意大利學習,至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回國,並曾
謁見康熙,且在北京等地傳教,1753 年(乾隆十八年)病逝。他著有《身見錄》,是中國人第
一部歐洲遊記。據統計,同治以前赴歐洲留學的中國學生共有 114 人。參方豪,〈同治前歐洲
留學史略〉,收入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學生書局,1969),頁 379-402。另外,
關於樊守義和他的《身見錄》,可參方豪,〈樊守義著中文第一部歐洲遊記〉,《中西交通史》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卷 4,頁 186-195。
23 Mr. Plumb 是 Mr. Plum 的轉化,因為這位翻譯是姓李的。參見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 320.
24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p. 270, 292;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41.
25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 291。
26 〈直隸總督梁肯堂等奏報接見使臣情形摺〉,《史料滙編》,頁 360。
27 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方豪六十自定稿》,頁 383、393。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4-
此外,這兩位譯員原是學習傳教的,沒有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中文水平不高。
斯當東曾批評過李雅各不諳中國官場文書風格,不能理想地完成翻譯的任務;28
也不熟悉官場講話的方式,有時候會把一些客套婉轉的說話理解為認真的承
諾。29
還有是這兩位翻譯官的國籍問題:他們都是中國人,卻為英國人服務和工
作,其中周保羅便因為自己私自離開中國,更為外國人工作而很感恐懼,在
1793 年 6 月使團抵達澳門後便匆忙離開。30就是留下的李雅各,顯然也感受到
沉重的壓力,他願意留下來,除了因為他相信假若發生事故,特使一定會營救
他外,還因為自己是屬於少數民族,樣貌跟一般漢人不太相像,因此,他特意
改換了英國軍裝,配戴軍刀,改用英國名字。31但這樣的喬裝並不成功,有一
次他替馬戛爾尼送信,雖然穿上英國服飾,但沿路還是被民眾騷擾和侮辱。32
不過,應該指出,從現在所見到的資料看,在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時,李雅各的
確很夠堅守崗位,沒有因為自己的中國人身分而感到為難或退縮。斯當東紀錄
了其中一次具體事件:負責接待使團的王文雄及喬人傑要求馬戛爾尼練習跪
叩,在遭拒絕後,他們指令李雅各示範,但李說他只會聽命於馬戛爾尼。33更
重要的是,儘管清廷也派來了一些西洋傳教士協助翻譯,但幾經討論後,中英
雙方還是決定在面覲皇帝時,由李雅各負責傳譯,原因是「他講的話是中國味,
終究比歐洲人講中國話更好聽些」。34由此可見,李雅各可以說是這次馬戛爾
尼出使中最主要的英方譯員。
不過,李雅各大概是很特殊的一位翻譯員。除了上面提到的周保羅在返抵
28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136.
29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30.
30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89.
31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89;不過,斯當東說李雅各生長在「被中國吞
併的韃靼地區」,便顯得很混亂,因為在別的地方,他也把滿洲人稱為韃靼人。結果,有學者
甚至直接把他說成是滿洲人,實誤,見 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p. 48.
32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 141;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255.
33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 90.
34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138.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05-
中國後便感到恐懼,馬上離開使團外,東印度公司也曾嘗試在廣州找到一名能
說西班牙文及中文的中國人,送到使團去協助翻譯的工作。35可是,他卻沒有能
夠完成任務。據斯當東說,他們曾把這位年輕人召來作翻譯,可是當他站在中
國官員面前時,便馬上害怕得不知所措,只管扮演下屬的角色,就是特使的說
話也用上最謙卑的言詞來翻譯。最後,他更寧願放棄高薪和到京城的機會,離
開使團。36由此可見,在這樣外交層面的翻譯裏,單單具備外語能力是不足夠的。
從現在所見到的資料看,使節團中還有別的人曾經協助過翻譯的工作。使
團從歐洲出發時,有兩名中國傳教士獲准隨船回國,其中一人叫安神父,據報
能夠寫得一手漂亮的中文,在船上幫忙翻譯和書寫文件。37不過,他在回到中
國後便離開使團,沒有再參與使團的翻譯工作。此外,斯當東的紀錄中還說過
到了澳門後,傳教士曾給馬戛爾尼介紹了一位能講中文和葡萄牙語的人作僕
人,原也是可以作翻譯的,只是在途中馬戛爾尼把他派到日本,最終也沒有隨
團到北京去。38然而,最有趣、也最廣為傳頌的是小斯當東的故事。
小 斯 當 東 全 名 叫 喬 治 ‧ 湯 馬 士 ‧ 斯 當 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是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他十五歲前一直沒有正式入學,只是
跟隨家庭老師學習,並以國內外的遊歷來增長見聞,這次是以馬戛爾尼的見習
童子(page)的身分跟隨父親到中國來。在航行途中,小斯當東跟隨翻譯官學習
中文,在很短的時間裏便取得成績。從馬戛爾尼以及斯當東的記述,我們可以
見到小斯當東在這次出使中國的行程中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譯者角色。他曾經正
式為使團提供過翻譯:當使團第一次和北京派來迎接的官員喬人傑及王文雄會
面時,由於人數眾多,翻譯人手不足,他便試著去做翻譯,效果很不錯;斯當
35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451.
36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14.
37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88.
38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509. 在斯當東這段敍述中,我們也可以見到馬戛爾
尼是非常重視翻譯人員的。斯當東說,馬戛爾尼為了將來要去日本,便要求人們尋找能通日語的
人,這個人如能懂日語,還能通任何一種歐洲語言,或者馬來語或中文,馬戛爾尼會不惜出重金
聘用。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6-
東在回憶錄中,也禁不住稱讚自己的兒子雖然學習上不夠勤快,但由於「感覺
敏銳,器官機能靈活,這次證明他是頗為勝任的翻譯」,39儘管他沒有點出小
斯當東的名字,但顯然是感到驕傲的。此外,我們知道小斯當東還曾經協助翻
譯出禮品單,40這是一項不可輕覷的任務,他們並不是要簡單地把禮品名稱開
列出來,因為這樣做是沒法顯出禮品的真正價值的,所以在翻譯時費煞苦心。
除實際翻譯工作外,小斯當東也在重要的時刻負責謄寫中文文件的工作,其中
一項是他謄寫了馬戛爾尼有關覲見乾隆時的儀式的照會。這份照會雖然由別人
譯成中文,但沒有中國人或朝廷派來的西洋人願意謄寫,害怕給人認出筆跡,
最後就是讓小斯當東來負責謄寫41─照會最後一句強調:「此呈係咤株士多
嗎嘶噹東親手寫」,42這並不虛假,因為謄寫的工作確是由他親手完成,只不
過不是由他翻譯罷了。除了這份重要的國事照會外,小斯當東在熱河時也曾謄
寫過一封馬戛爾尼口述、一名中國人翻譯給和珅的信件。43
此外,他曾經和乾隆直接以漢語交談。當使團在熱河獲得乾隆的接見時,
由於談話要經過幾重的翻譯,乾隆覺得很不耐煩,詢問使團中有沒有能夠直接
講中國話的人,馬戛爾尼便引見了小斯當東。我們並不知道談話的具體內容,
但據斯當東的回憶錄:「或者因為這個童子的講話使皇帝滿意,又或是見他活
潑可愛」,乾隆從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賜給小斯當東。44對此,斯當東還
作了一個很準確的評論:
荷包是中國皇帝經常賜贈獎賞大臣的禮物。但從皇帝身上直接解下的
荷包更是非常特殊的恩典。皇帝身上的任何物件在中國都認為是無價
39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489.
40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p. 100.
41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142.
42 〈英多馬斯當東手書漢字副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收入《史料滙編》,頁 232。
43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253.
44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234;其實,小斯當東還在萬樹園得到乾隆其他
的賞賜,包括布疋、茶葉、磁器及荷包等。見〈擬於萬樹園賞副貢使之子多馬斯當東〉,收入
《史料滙編》,頁 150;另外,他在各處參觀時也得到賞賜,參見〈副貢使之子等在含青齋等
處瞻仰酌擬賞清單〉,同上,頁 105。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07-
之寶。一個外國小孩得到這個殊榮,引起當場所有中國官員的注意和
羨慕,甚至有些人還會妒忌起來。45
後來,小斯當東還親手寫了一封感謝信給乾隆,筆跡看來雖明顯是稚嫩的,文
句也不很通順,但以一個年僅 13 歲,初學中文不久的外國孩童來說,那已經
是寫得很不錯了,46由此也可以估計他當時的口語也應該說得很好,所以能夠
贏得乾隆的歡心。
我們知道,這位因為能說中國話而得到乾隆賞賜的小斯當東,後來再次來
華,成為東印度公司的大班(supercargoes)及商館決策委員會的秘書、「特選管
貨人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的主席。更有趣的是,他在嘉慶
二十一年(1816)跟隨阿美士德爵士(William Lord Amherst, 1773-1857)使團,以第
二副使身分再一次到北京。此外,他也是英國最早的一位漢學家,曾經翻譯出
版過《大清律例》,47並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共同創立英國亞洲皇家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毫無疑問是中英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然而,必須強調,他的漢
語能力原來是早年跟隨父親和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所開始掌握的。
45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234-235.
46 這封感謝信並沒有收在《史料滙編》內,影印件見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392。不過,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該書對信影所作的題註竟然
是「由副使斯當東親筆書寫的致皇帝感謝信」,這明顯是錯誤的,一來副使斯當東不懂中文,
二來信影中清楚寫著「此呈係多嗎嘶噹東親手寫」─「多嗎嘶噹東」就是小斯當東。此外,
據斯當東的記述,就是乾隆也覺得小斯當東的中國字寫得不錯,更曾經叫他以毛筆繪畫。雖然
小斯當東從來不會繪畫,但勉強畫出來後,「皇帝看了非常高興,又給了他幾樣禮品」。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I, p. 267.
47 George T.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T. Cadell & W. Davis, 1810; repr.,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66);關於斯當東的生平,可參他的自傳: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 Lydia L.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Unpublished MA thesis, Duke University, 1968);有關斯當東翻譯
《大清律例》,可參見 James St. André, “‘But Do They Have a Notion of Justice?’ Staunton’s 1810
Translation of the Penal Code,” The Translator 10:1 (April 2004), pp. 1-32;侯毅,〈喬治‧托馬斯‧
斯當東眼中的《大清律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及蘇州大學社
會學院編,《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496-510。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8-
三
在上一節裏,我們介紹了代表英國使團的翻譯人員,那麼,中國方面又派
出了什麼人來進行翻譯的工作?
我們知道,馬戛爾尼來華的消息,早在使團出發後不久便透過廣州洋商蔡
世文傳達到署理兩廣總督郭世勳,並立刻上奏乾隆。乾隆對此次遠人航海而來
十分重視,連續幾次下旨沿海各省總督及巡撫等作好準備,迎接英使。48可以
想像,地方官吏對此更是緊張,尤其是廣東地區的官員,他們特別害怕英使團
訪京的目的跟洪任輝一樣,是要投訴廣州的對外貿易,因此,他們很著意地要
派人跟使團儘早聯絡。他們最初希望英使團能改變計畫,先到廣州,而不是直
接去天津,在遭到拒絕後,他們又嘗試委派譯員陪同特使進京。根據斯當東的
記述,廣東的官員曾經通知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他們已安排好兩名廣東商人
隨時候命,待接到特使到達的消息後,即趕赴特使到達的口岸,迎接使團,並
擔任使團的翻譯。49
這是我們知道最早從中國方面所安排的翻譯人員。顯然,廣東地方官吏所
能調動的翻譯人員,其實就只是那些一直以來在廣州利用極度扭曲的洋涇濱英
語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洋商和通事,這便是他們全部的外語人才資源了。不過,
這兩名廣東商人最終並沒有出現,一方面是東印度公司婉拒了這項安排,因為
他們很清楚知道這兩名商人的英語能力太差,絕對無法充任翻譯;另一方面是
這兩名廣東商人自己也不願意擔任這工作,他們在廣州的商務利益很大,既不
想離開,又害怕捲入中英的外交瓜葛,尤其更擔心英特使會在北京投訴廣州的
通商情況,恐怕會被視為同謀,因此極不情願出任使團的翻譯,最後是透過賄
48 英國使團是在 1792 年 9 月 26 日出發的,而兩廣總督郭世勳則在同年 10 月 18 日接到蔡世文等
人的稟報,4 天後,郭世勳聯同粵海監督盛住上奏皇帝,乾隆在 12 月 3 日傳諭各督撫護送英使
進京。參〈諭軍機大臣著傳諭各督撫如遇英貢船到口即速護送進京〉及〈諭軍機大臣著傳諭沿
海督撫妥善辦理迎接英貢使事宜〉,收入《史料滙編》,頁 27-28。
49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95.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09-
賂官員才得以豁免。50
不過,當使團的船隊到達舟山的時候,一些官員來到船上探看情況,仍帶
了一個當地的商人作為翻譯。同樣地,這名翻譯原來也是在舟山還允許與外國
通商時,透過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而學會英文的。據報導,他「還記得幾句英
文」,似乎能夠勉強完成任務,使團成員也能從這名翻譯得到一些信息。51然
而,這大概也就是地方官員所能找到最好的翻譯人員了。
可是,天津和北京的情況便不一樣,朝廷在外語資源上便豐富得多。本來,
清初沿習明舊制,設有會同館及四譯館,分別主理朝貢及翻譯事宜,52但乾隆在
十三年(1748)頒布諭令將四譯館歸併於會同館,稱會同四譯館,原因在於大部
份的朝貢國如朝鮮、琉球、安南等「本用漢字,無須翻譯」,因而「該館並無
承辦事務」。53不過,當外交活動涉及的是西方國家時,情況就很不同,翻譯
的工作不可能由四譯館的通事負責,而協助清廷作外交翻譯的卻是一些西方人
─從明代以來便來華留京的耶穌會教士。54這些耶穌會士大都通曉多種歐洲
語言,且對歐洲國家的情況十分熟悉,因此便成為朝廷與西方國家交往時的重
要橋樑,不只擔任翻譯,且往往起著外事顧問的作用。55例如,湯若望(Johann
50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Vol. I, p. 396. 季壓西說:「東印度公司廣州委員會只好
花了一大筆錢,賄賂廣州官吏,告訴他們『馬戛爾尼勳爵已從歐洲找到適當的翻譯一同前來』」,
實誤。季壓西、陳偉民,《中國近代通事》,頁 14。
51 季壓西、陳偉民,《中國近代通事》,頁 416。
52 永樂五年(1407),明成祖下旨成立四夷館,設通事等的職位,負責翻譯。另一方面,會同館原
屬設於京師的驛館,是「專以止宿各處夷使及王府公差、內外官員」的接待機構,亦設有通事,
負責譯審、伴送外國和少數民族使臣。關於四夷館資料,可參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
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112-120;Norman Wil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su I Ku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 (1945),
pp. 617-640.
53 〈禮部‧朝貢‧象譯〉及〈禮部‧朝貢‧館舍〉,《清會典事例》,卷 514,錄自李云泉,《朝
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頁 179。
54 由於與俄羅斯的接觸較多,清廷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便開設了俄羅斯文館來培訓俄語翻譯
人才,且一直在運作,但似乎成績不理想,至同治元年(1862)俄羅斯館遭廢除,翌年在京師同
文館內增設俄文館。〈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總理各國事務奕訢等奏〉,中國史學會主編,《洋
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冊 2,頁 13。關於俄羅斯文館,可參見蔡鴻生,
《俄羅斯館紀(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55 參余三樂,《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 14、173-17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10-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便曾在順治十二年(1655)荷蘭使團訪京活動
中擔任翻譯,更向朝廷提出意見,把荷蘭人拒諸門外;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康熙十五年(1676)處理俄羅斯使者尼古拉的到訪,以及
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蘭的另一次使團來訪活動中任翻譯,都得到很高的評
價。耶穌會士在清外交史上最重要的貢獻,是葡萄牙籍的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和法國籍的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作為中
國談判使團的成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參加與俄羅斯談判和簽訂《尼布楚
條約》,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西方國家簽署的條約。在這次外交活動
中,耶穌會士所扮演的是遠遠超出翻譯的角色,56更因為他們的忠誠和功績,
天主教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取得了在中國公開傳教的權利。
不過,一場「禮儀之爭」導致了康熙在五十九年(1720)下旨禁教,57而 1723
年登位的雍正更是厲行禁止,隨後的乾隆也是積極禁教的。但儘管這樣,清廷
所本的是「重其學,不重其教」,繼續任命耶穌會士在朝廷工作,就是乾隆也
願意承認「北京西士功績其偉,有益於國」。58
在馬戛爾尼訪華使團來華的時候,還有為數不少的耶穌會士在北京為乾隆
工 作 , 當 時 擔 任 專 門 翻 譯 西 方 語 言 的 是 法 國 耶 穌 會 教 士 錢 德 明 神 父
(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他是一位數學家、物理學家,法國科學
院與英國皇家學會的通訊院士,早在 1750 年便來到中國,被視為北京傳教士
56 例如,康熙便曾對耶穌會士說過:「和約得以締結,實賴爾等之才智與努力,爾等為此事出力
頗多。」《徐日升日記》,轉錄自江文漢,《明清間在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上海:知識出
版社,1989),頁 77;另外中國使團的首席代表索額圖也說:「非張誠之智謀,則議和不成,
必至兵連禍結,而失其和好矣。」錄自余三樂,《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頁 275。關於這
次談判,可參 Joseph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1961);張誠,《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
館,1973)。
57 關於這場中國與梵帝崗教廷間的禮儀之爭,可參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蘇爾(Donald St. Sure)、諾爾(Ray Robert Noll)編,沈保義等
譯,《中西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1645-1941)》[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8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783。
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
-111-
的精神領袖。59不過,在馬戛爾尼來華期間,錢德明已患病,不能前來探訪使
團成員,只寫過一封信來,表示願意提供資訊及協助,但他在使團離開北京後
兩天便病逝,沒有參與過這次使團的活動。清廷派來參加這次接待使團的傳教
士有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安國寧(André Rodriguez,
1729-1796) 、 賀 清 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 潘 廷 璋 (Joseph Pa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