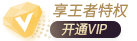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doc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要】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摘 要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史学理论
【关 键 词】新史学/史学史/历史学者/主体意识/孔子/司马迁/郑樵/梁启超
【正 文】 今年第10期是《史学月刊》创刊第300期。《史学月刊》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31日,其创办人嵇文甫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会长。1957年改名为《史学月刊》,并由郭沫若院长题写刊名。《新史学通讯》是中国史学乃至国际史学上第一份正式以“新史学”命名的专业史学刊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一家史学期刊。从中国史学发展史角度讲,《新史学通讯》所追求的“新史学”,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从渊源上可以说是“新史学会”在共和国初期发展的一个产物。“新史学会”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以唯物史观为指针研究和著述中国历史”,嵇文甫先生是其初创者和组织者之一。(注:参见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共和国成立后,嵇文甫先生任“新史学会”的河南省分会会长,并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因此,由他创办一份以“新史学”为名的专业史学刊物,是很自然不过的。从整个国际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新史学通讯》可以看做是国际史坛“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这种学术渊源和国际史学背景,使得《史学月刊》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把追求新史学、宏扬新史学和培植史学新人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月刊》的这一宗旨,与史学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和一般形态是正相吻合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历史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股史学思潮均以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为旨归。 在欧洲,“新史学”批判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以政治史叙述为中心、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为认识论与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论特征的兰克史学。“其
代表者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m Dilthey, 1833,1911)、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在意大利有克罗齐,在英国有特里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等等。20世纪前期的英国学者柯林伍德也属于这个行列。”[1] (p10)在史学任务上,“新史学”者反对把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史学观,认为史学“研究个别事实”,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研究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新史学”者反对传统史学的纯客观主义的观点和做法,强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的主体性作用和史学的主观性人文特性,“有的甚至认为,‘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1] (p10) 在美国,1898年,密执安大学E. W. 道(Earle Wilbur Dow)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上发表《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 Apropos of Lamprecht’ s” Deutsche Geschichte” ),最早在公开刊物上使用“新史学”术语,(注:单从词语来看,最早提到“新史学”(Une nouvelle historie)的,是法国哲学家Henri Berr在189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而在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认为《新史学》的作者鲁滨逊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新史学”一词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并被用于指称不同于兰克史学的历史学新趋向,但真正使“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并对“新史学”的特征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新史学”看来,“政治现象不是历史学对象的惟一,国家也不是统御万物的因素”,只有“人类生活中某种自然的、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才是“基本的”,因为正是“这些因素的本质、转变和相互联系,构成了某个特定时代的文明”。鉴此,“新史学是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加以考虑的”,“新史学……坚持从理性进化的视角描写人类历史的法则”,[2] (p4,5)提倡用动态的过程分析代替静态的现象描述。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詹姆斯?H.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出版了《新史学》一书,对“新史学”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1929年,西方“新史学”公认的权威性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创刊。这标志着“新史学”在西方史学界的正式崛起。 在中国,1902年,梁启超署名以“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20号发表《新史学》,批判传统中国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三恶果”,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和进化史观,呼吁进行一场“史界革命”,期望中国史学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能够肩负起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
历史重任。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它不仅是“国民之明镜”,而且是“爱国心之源泉”。因此,中国史学若要在型塑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必须进行一场“史界革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只有通过“史界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才能“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亦才能使史学本身成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如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学科。[3] (p1,7)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新史学》……[因此而]成为中国近世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4] (序言,p2)。 研究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学者指出:“一般说来,‘新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说法,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学新趋势,它展现了有别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狭义的‘新史学’,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叛以考证手法和叙述政治史的传统史学。”[2] (p2,3)除此而外,也有“特指”意义上的“新史学”,如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重点的美国新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新史学通讯》为代表的中国唯物史观派新史学。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新史学”,“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之处,主要在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 作为一个史学术语和概念、一个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即打上了引号的“新史学”,我们可以说,“新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所特有的。但是,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事实上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如果没有新史学的不断涌现,那么史学就是僵化的,就谈不上发展,也就无所谓拥有自己的“史”,因为历史的本质属性就体现在变化、运动和发展,表现为新老交替的流变过程。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作为一种史学现象,新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史学创新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史家主体意识;并且,这种意识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学者史学实践的成功与否及其史学成就和史学贡献的大小。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样式,至多只是一个模糊的大致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史学上的经验事实,(注: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笔者
主要以瞿林东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为据。瞿先生的著作使笔者受益颇多,在此特向瞿先生深表谢意,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对作为一种史学现象的新史学做初步的探讨,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一 新史学: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历史学者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或者说,“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为人类“一般意识形态”活动的“现实前提”,[5] (p67)那么,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的史学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即一些现实的个人对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记录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个人的有意志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是一般意识形态活动的现实前提,而且正是历史的基本内容。没有对这些历史的基本内容的记录,也就不可能有对“一些现实的个人”的有意志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认识、概括和解释,即对历史的内容进行研究的史学活动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般认为,人类最初的记录自己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方式,是原始的“口述史”。事实上,除了原始的“口述史”方式之外,确切地说,与原始“口述史”相辅而行的,还有原始舞蹈。已故孙作云先生关于中国傩戏史的研究表明,与图腾信仰纠缠在一起的“打鬼跳舞”,其原始意义和形式就是指黄帝战胜蚩尤的历史。[6] (p364,368)这就是说,人类初期对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记录,既有语言的形式,也有形体的形式,两者往往是互为辅助的。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历史记载的形式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文字记录逐渐成为历史记载的主导和主流形式,但“口述史”的历史记录方式仍一直存在着,而形体的历史记录方式则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而失去了其原初的历史记录性质。由于文字的掌握及其书写需要必要的训练,且被视为一种极其神圣的活动,因此历史记载也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以记载历史作为主要职责的史官应运而生。在中国,春秋末年以前,史官一直垄断着历史记载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典册,如《尚书》中的殷商、西周人记载和《逸周书》中的西周人的记载。[7] (p125)这些历史记载,既有对过往历史的追述,也有对当时王朝重大事件的记录。当然,除了史官的历史记载活动外,也还有其他的历史记载活动存在,例如,《诗经》中具有史诗性质的《雅》、《颂》,而《风》更是对当时人特别是民间人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的生动而真实的记录。不同形式的历史
记载活动的存在,为史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现实前提。 单纯的历史记录不等于史学。史学区别于一般历史记载的地方在于“史义”,用现代史学概念来说就是“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解释是历史[学]的生命必须的血液。”[8] (p26)“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纪(记)载,而在于评价。”[8] (p18)换言之,历史记载向历史学的转变,是通过历史学家赋予历史记载以一定的“义”,并按照一定的“义”对既有历史记载进行重新编排和解释来实现的。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主要依据鲁国“史记”,修成编年体史书《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诞生。《春秋》之所以是中国史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它本质上区别于以往历史记载之处,就集中体现在它具有孔子所赋予的一定的“义”,承载了孔子个人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社会理想,是孔子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产物。 从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考察,一方面,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历史记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史学的诞生准备好了沃土,如早期的甲骨文和金文记事,官文书(王家的训诫、诰誓等),特别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发达,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史学的正式产生准备了丰富资源;另一方面,到了春秋末年,由于历史的大变动特别是私人讲学和撰述活动的出现,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的王、侯贵族,都已经不再能垄断历史记载活动,而原有比较单纯的、流水账式的历史记载亦不复能够满足人们探询历史、特别是思想家们构建思想体系的现实之需。因此,历史记载向史学的过渡并且仅作为史学的现实前提而存在已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历史的客观要求必须通过“一些现实的个人”的创造活动才能成为现实。正是对现实保持着敏锐观察且“好古敏求”的孔子,承担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创立者的历史角色并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对于把历史记载转化为史学这一前无古人的巨大的史学创新活动,孔子有着自觉的认识。从孟子对孔子修《春秋》这一历史活动的经典性评述中,可以发现,孔子之修《春秋》,不仅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而且他赋予了自己的这一历史活动以强烈而鲜明的现实性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性,寄托了他个人的全部政治思想、社会理想,一句话,他把自己全部人生追求都浇铸进了《春秋》之中。在《滕文公》篇中,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就是说,孔子是鉴于当时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的君主和儿子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事情屡有发生的严酷社会政治现实,并为此而深感忧虑,[9] (p139)——在此自觉的主体意识下,才修撰《春秋》一书的。由于在编修《春秋》一书的过程中,孔子把
自己的社会理想融会进了该书的叙事之中,因此孔子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无论是了解他的人还是责怪他的人,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依据,拿《春秋》来说事。这表明,无论是对于修《春秋》这一行为本身,还是对于这一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孔子都是有清楚的思想认识的,也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而孟子则直接道出了“孔子成《春秋》”对于当时社会政治所可能产生的客观影响——“乱臣贼子惧”,并把孔子成《春秋》这件文化盛事直接与过往历史中的两大壮举——“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驱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9] (p140)——相提并论,认为孔子成《春秋》这一史学创新的文化行为与禹、周公的政治行为一样,具有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巨大历史意义。这反映了孟子对史学创新活动的深刻认识。 不宁惟是,而且孔子对于自己所修的《春秋》与以往历史记载特别是史官的历史记载的根本区别,也有明确的认识。《春秋》一书,所叙述的事情与史官的文字记载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即主要是一部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在当时,像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和孔子据以修史的鲁国的《春秋》,都是如此。但不同于这些出自史官之手的“国史”的是,孔子从既存的历史记载中,私下取用了它们的大义。对此,在《离娄》篇中,孟子这样评论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9] (p178,179)正是孔子的这一夫子自道,揭示出了史学与一般历史记载的根本不同之处:一般的历史记载只是对人们的有意志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简单的文字记录而已,史学却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所记录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意义,或者在叙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应当赋予一定的思想意义。概而言之,一般历史记载重在记录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史学则在此基础上重在揭示出并解释被记录下来的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所具有的某种“大义”。 研究孔子思想,一般把《论语》作为基本的材料。但孔子的自述和孟子的评论表明,至少对于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而言,首要的材料不是《论语》,而应是《春秋》。历代《春秋》学学者孜孜于探询孔子所赋予《春秋》的“大义”,显然不是无的放失的徒劳之举。对于本文之目的来说,这已是题外话。就本文主旨而言,从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过程和孔子自觉的史学创新活动中,可以发现的是:一种新史学的诞生,是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历史学者积极主动的史学创新、追求新史学的主观努力相互作用的结
果。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形态或模式。司马迁、班固创建中国“正史”《史记》、《汉书》两大模式,刘知几以《史通》开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范式,杜佑以《通典》开典制史之先河……直至近代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上以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为“共通点”[4] (p672)的各种“新史学”学派的涌现和唯物史观派的形成等,莫不遵循着史学发展的这一基本模式。 在中国史学史上,每当一种史学范式甚至只是史学形式的历史编纂体裁不能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内容的时候,新的史学范式或历史编纂体裁经过一定时期历史学者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历史形势的需要,满足人们对历史的新认识和探询越来越深入的要求。下面以《史记》为例来说明之。 秦汉时期,“海内一统”,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使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于诸侯国林立、群雄争霸的社会政治格局的各国为史的“国史”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生活于一统之下的人们,首先是统治阶层,也不再满足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而要求对包括以前各国历史在内的整个过往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是,政治一统的需要使统治阶层开始认识到禁止人们止观国史的重要性,以便消除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形成的强烈的以国属为核心的地方意识。秦始皇从消极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销毁除秦国史记之外的其他国史的政策。然而,“坑灰未冷山东乱”,其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强化了人们特别是六国贵族余孽的地方意识,秦王朝最终也被地方意识的巨浪所吞噬,落得个二世而亡的悲剧。历史实践否定了秦始皇消极的史学政策,那就只有采取积极政策。这就要求史学突破“国史”的局限,要求历史学者编纂出一部包括七国历史在内的反映整个过往历史的“通史”。《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是在史学的这种内外客观要求下催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史记》不单单只是一部历史著作而已,它实肩负着当时消除世人的“战国意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归属意识(或可以名之曰“大汉意识”)的历史使命。 新史学的诞生是以继承史学创新者所直接面对的史学文化遗产为前提的。在《史记》的产生过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作为一堆废物而被开创“通史”这一史学新范式和历史编纂新体裁的司马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相反地,秦汉以前已经出现的史学表述形式,如“本纪”、“世家”、“传”等直接成了司马迁进行史学创新活动的资源,有的如“谱”等则经过一定的改造而转化成为新的、成熟的历史表述形式。对此,司马迁自己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自谦地说道:“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0] (p3299,3300)梁启超则评论说:“迁书取材于
《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11] (p18,19) “通史”这一史学范式,在秦汉时期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式;将已有的历史编纂体裁直接或经过一定的改造后融于一史之中,这种“综合体”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来说,同样也是“新”的。当然,司马迁不只是一个无所自创的集大成者而已。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来说,在史学上有所创新是其本质特征。司马迁也不例外。自不必说他运用广泛的田野调查以补当代史研究史料之不足而开创了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新史学方法,也不必说他创立了历史评论的“论赞”形式,即以梁启超所断言的“非皆迁所自创”的诸体来说,包括梁启超在内,绝大多数史学史学者其实都忽视了《太史公自序》这一史学“自序”体裁在史学发展特别是史学评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司马迁之前,没有用专门的“自序”的形式来阐述历史学家撰史的动机、旨趣和自己的历史著作内容的。通过孟子的引述,我们看到,孔子对于自己修《春秋》的行为及其旨趣曾有过自我评论,且深刻地揭示了他所修的《春秋》与一般历史记载的根本区别所在。但这方面的言论,并没有直接反映在《春秋》一书中,更没有以专篇的形式作为自己的历史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列于其中。司马迁开创了这一先例,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笔者以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活动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都承认,史学评论实践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孔子对宋、杞两国所保存下来的关于殷、夏两代历史材料的评论,孔子之后则有《左传》作者、孟子、荀子等史学家、思想家或政治家对于孔子所修《春秋》的评论。但正如研究者们所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评论活动大多停留于就事论事,且或从属于政治评论,或依附于思想家的社会理论、政治学说或哲学思想,它们虽然对后世的史学发展和史学评论活动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但针对个别史学著作所作的评论本身,并不是立足于史学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则不然。它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篇由历史学家撰著的史学评论专文,开创了史学评论中“自我”评论和“为我”评论两种基本形式。《太史公自序》首先以“自我”评论的方式叙述了作为《史记》作者、历史学家司马迁个人的家族、身世和学术渊源,借以表明家学和师承渊源对于历史学家成就史学伟业的重要性;然后以“为我”评论的方式,从总体
上评论了先秦学术,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论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春秋》,以阐明《史记》对已有史学成果的继承和史学思想渊源;最后又以“自我”评论的方式概述了《史记》的内部结构以及各篇的具体撰述旨趣。这是一篇典型的以自我评论为主、有机地融合了为我评论的形式的史学评论专文。它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学家自觉的、独立的史学评论的产生。而“自序”这一阐述历史学者撰史的动机、旨趣和自己的历史著作的内容的史学评论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见,司马迁所开创的历史学者“自序”,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只是我们习焉而不察罢了。 从编年体国史到纪传体通史再到纪传体皇朝史,从一般性通史到专门叙述典章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沿革的典制体通史,从纪传体到纪事本末体,从“正史”一枝独秀到地方史、民族史、域外记述、家史、谱牒和别传等史学多途发展,历史知识从只是上层统治阶级藏之名山、秘而不宣的治国宝典到走向社会深层、成为一般市民阶层也能享受的公共知识,[7] (自序,p4,6)——正是在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局限、不断地自我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内容,扩大着自己的受众面,丰富着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指导观念。一部中国史学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部新史学不断涌现的历史。 二 新史学:历史学者成功的关键
史学的发展体现在新史学的不断产生。新史学的产生,固然是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自身的内在要求,但这种要求能否成为客观现实,成为一种“实然”的东西,关键在于作为史学主体的历史学者追求新史学的主观努力的程度。因为,史学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样,毕竟是由现实的个人来进行并完成的。而历史学者追求新史学的史家主体意识的强弱及其主观努力的程度,则极大地决定着历史学者史学实践的成功与否。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及其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在客观前提具备的条件下通过孔子、司马迁等伟大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努力实现的。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也不乏相反的例子,即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史学自身的发展对史学提出了某种新的要求,并且这种新要求已经为敏锐的历史学家所觉察,但由于后世历史学家思想的迟钝,没有付诸实践,史学自身发展对于新史学的要求便迟迟不能得到满足。对新史学要求熟视无睹或反应迟钝的历史学者,在史学史的长河中,不是成了匆匆的过客,就是让本应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史学成就的天赐良机白白地从自己身边溜走、从而让“伟大历史学家”的荣誉与自己擦肩而过。 例如,到了唐代中期,一方面因为客观历史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因为史学自身的发展积累,在“国史”即纪传体皇朝史的书志中增加诸如“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等新内容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客观
历史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草市”基础上兴起的市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京邑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了起来,具有了为其他市镇的发展提供“准则”的功能,所谓“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12] (p126)。从京城的建筑样式到其市民的生活方式,都成为京外市镇追慕的对象。这在今天亦复如此。从京城本身即狭义的方面来说,“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一代帝王在宫殿的规模式样和朝廷的仪式法度方面的所作所为,对于后世帝王也有准则的效用。在都邑建设中,“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即都邑建设中不好的方面可以警诫世人,好的方面则可以劝勉后代。因此,作为“正史”的“国史”,理应对都邑的历史予以应有的关注。第二,魏晋以来,一方面是门阀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永嘉东渡,流寓扬、越”,出现了“南北混淆”即南北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同时“华壤边民,虏汉相杂”,即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使中原地区出现了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参杂的局面。门阀制度要求氏族的发展脉络一清二楚,而南北民族的大融合势必要打破氏族的清纯发展。到了唐代中期,一方面在原有高门望族的基础上,新的宗族势力发展起来,出现了“非复一家”的“高门素族”,一方面则因门阀制度的松弛特别是民族融合而出现了“不识其先”的社会现象,[12] (p130,131)这对于一向注重宗族血统渊源的中国人来说,难免会被人讥为春秋时期晋国的籍谈那样的“数典而忘其祖”者。第三,魏晋以来南北民族的融合带动了南北交通的发展和物产的流通,而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人们对各地的物产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大唐与周边政权甚至远至欧洲的政权都发生了关系,域外物产不仅作为贡物大量进入统治阶层的生活,而且出现在市场上而为广大市民所认识。历史编纂如何适应并反映这些变化了的客观历史内容,成了摆在当时历史学者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 从史学自身的发展积累来说,对于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的都邑、氏族、方物等,“诸史”虽然“竟无其录”,但“正史”之外的其他历史编纂或记载,并没有对发生深刻变化了的现实的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漠然视之。刘知几在批评历代“正史”的书志对于都邑、氏族和方物“竟无其录”之失的同时,就指出,金石、草木、丝麻及其织品之类,鸟兽、虫鱼、象牙、皮革、羽毛之类,早在《夏书》的《禹贡》、《周书》的《王会》篇中,就有记载,而禹用九州贡钢铸的九鼎更是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记载了九州的方物;就都邑方面的历史论述而言,远则有汉代的《三辅典》(或疑即谓《三辅黄图》),近则有隋代的《东都记》,南朝的《南徐州记》、《晋宫阙名》,北朝的《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等;氏族史方面,汉有赵岐的《三辅决录》,西晋有挚虞的《族姓
记》,东晋有王俭的《百家集谱》和王僧孺的《百家谱》,等等。[12] (p129,134)在刘知几看来,只要跳出“正史”的范围,放眼整个史学,就可以发现,对于都邑、氏族、方物这类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三代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汉代以来更是代不乏人,到了近代尤呈发达之象。 鉴于上述,刘知几建议:“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12] (p127,129,131) 刘知几关于在“国史”的书志中增加都邑、方物、氏族三志的建议,是从客观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和史学发展自身的要求出发的,认为历史编纂的内容必须随着客观历史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行新的取舍。但他的建议是以史学评论的方式提出的,对于都邑、方物和氏族三史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很不充分,甚至眼光颇为狭窄。特别是,作为史家,他自己并没有把这些拓展史学内容的要求付诸具体的史学实践,从而丰富“国史”的内容,实现“国史”的新发展。从刘知几的史学实践来看,他曾担任过史官,撰起居注,后又任著作佐郎等职而与修国史,但他在新史学方面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发展的贡献上,即开创了以史学评论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古典史学理论的发展道路和形成了一套体系比较完整的史学评论方法。 刘知几之后,修撰“国史”的历史学者对其意见或多或少有所采纳,如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就在《地理志》的志首概略地叙述了唐两京宫观苑囿的情况,志中还兼载各地的物产名目;《宰相世系表》则以“表”而非“志”的形式列出了几个世家大族的源流情况。[12] (p91)但欧阳修等人的史学实践,都没有使都邑、方物和氏族的历史获得独立的地位,它们依然只是其他志的前缀或附丽。直到南宋史家郑樵撰《通志》一书,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上述三个领域,才真正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表述形式。 郑樵《通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二十略》。《二十略》不仅将刘知几建议的氏族、都邑各立为独立的一略,从而使这两个领域的历史在史学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且他进一步将“方物志”细化和改造为“金石”、“昆虫草木”二略。这四略的立目和内容,虽然刘知几在史学评论中曾经提及,但都是以前史书诸志不曾专门论述的,属于郑樵自创。《二十略》中除此四略外,属郑樵自创的还有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五略。作为郑樵追求新史学的突出成果的这九略,不仅涉及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两门学问、关于政治地理的学问,而且提出了历史文献学范围的新领域,扩大了人们对自然史的认识和研究的范围。[7] (p462,463)《二十略》共52卷,而属于郑樵自创的九略有20卷,占1/3以上,足见作者对它们的重视。 郑樵追求新史学的努
力不只突出地表现在九略的创立,也表现在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其他方面。例如,《二十略》以《氏族略》始,继之以《六书略》、《七音略》,复继之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最后终之以《灾祥略》和《昆虫草木略》。这种内容安排及其所体现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就历史意识而言,将《氏族略》居于首位,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氏族(亦即宗族)为纽带而组成的社会,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作者对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深刻认识——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人首先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人的社会性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氏族略》之后继之以六书、七音二略表明,在作者看来,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人是一种有文化生命的动物。而天文、地理和都邑三略,无疑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平台,同时它们也是展开历史活动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以自然界的现象和物产而结束,也就昭示着人类历史活动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就是人与自然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互动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说宋代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奇葩,那么《二十略》逻辑结构背后所隐含着的这种历史意识,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典史学历史意识的最高成就。就史学意识而言,如上所述,无论是《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还是《昆虫草木略》,都属郑樵自创。始之以自创,终之于自创,这充分反映出郑樵对史学创新的高度重视。在作者的史学意识中,史学的生命力正体现于超越前人史学成就的史学创新。 对于创新史学,郑樵是有自觉而清醒的思想认识的。在《通志?总序》中,郑樵颇为自得地说:《二十略》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它们“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其余十五略,则“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瞿林东先生研究后指出:郑樵所谓“非诸史之文”并不完全合乎事实。[7] (p462)笔者以为,重要的不在于郑樵的自诩与事实不完全相符,而在于它表明,郑樵是以不剿袭旧说甚至不照搬“旧史之文”的史学创新精神,来作为自己史学实践活动的基本准则和努力方向的。如果没有对新史学的自觉而强烈的追求,郑樵不会劳神费心地去改“志”为“略”并将其界定为“总天下之大学术”的“纲目”,他完全可以采用现成的术语,如“志”(司马迁)、“书”(班固)、“意”(蔡邕)、“典”(华峤)、“录”(张勃)、“说”(何法盛)等[7] (p461);自然更不会有新创九略的出现。因为,自刘知几提出“国史”应为都邑、氏族、方物独立立志以来,在450年左右并不算短的历
史岁月里,并不乏历史学者,甚至不乏像欧阳修那样洞悉刘知几史学建议的历史学者,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完成刘知几的心愿。只有郑樵,不仅完成了刘知几的心愿,而且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历史论述的范围,使人类历史活动的诸多领域在史学上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说,郑樵之能够与司马光并立而成为两宋史学上的“双子星座”,[7] (p466)实源于他对新史学的孜孜追求。 郑樵的事例表明,历史学者的伟大与平凡,关键就在于其史家主体意识之强弱;而史家主体意识之强弱,则集中表现在其追求新史学的意识的强弱。一个历史学者,若缺乏追求新史学的主体意识,满足于人云亦云,满足于“旧史之文”,安于既有的史学范式或历史编纂形式,那就只能流于平庸。对新史学持之以不懈的追求态度,把创新史学作为自己史学实践活动的基本准则和奋斗目标,是每一个历史学者应该承担的职责。在追求新史学、创新史学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每一历史学者都会取得成功,跻身于伟大的历史学家行列。但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成不了一个好士兵。同理,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者,同样也成不了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因此,新史学,理应成为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三 新史学:边界模糊而方向明确
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一般而言,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但它作为历史学者努力追求的方向却是明确的。 2002年8月,借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百周年之机,北京的一些学者发起了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据会议组织者称,之所以发起这样一次“纪念”活动,一方面是考虑到,“从《新史学》发表到现在已整整百年之际,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清理《新史学》及梁启超相关论述中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不仅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史界共同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为要“对如下现象作出一种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的学者纷纷介入历史学界,历史学变成了不同学科诠释各种现象的‘殖民地’和最大的‘公共领域’”。[4] (序言,p1,2)为此,会议发起者特意邀请到了分布于历史学、文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等九个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会后,出版了厚厚两册的包括研讨会会议录音整理在内的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会议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主旨是想在新世纪之初为中国的新史学规划出一个具体样式,结果却只是取得了一幅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会议上“不失理性地相互交锋辩论”自不必说,从文集来看,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问题,的确也仅仅是各学科“代表性学者”的自话自说;即便是与会的历史学者,也没有能够就中国所需要的“新史学”的样式说出个子丑寅卯
来。其实,对于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期望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新史学的具体样式,是一个漫长的史学创新过程的结果,并非一开始就有一个样式、一种模式呈现给人们以供仿造。而且,一旦清晰可辨的新史学样式形成,它也就成了被超越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表明,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学者对新史学有了更加自觉、强烈和明确的追求,并昭示出了新史学努力的一些方向。从史学史上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主要是方向性的。新史学方向的选择和确定,一般地通过对既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而获致。在中国史学上,这样一条新史学前进之路,笔者以为,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开始开辟出来了。时至近代,中国“新史学”开山梁启超同样走着司马迁的路子。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口号,固然如论者所言有其明显的西学背景(以日本作为中介),[4] (p671)但他提出的方式却依然是传统中国史学式的,即通过对中国既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的路径来提出“新史学”主张。 在梁启超看来,传统中国史学存在着“四弊”和由此而生的“二病”。所谓“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即“难读”、”难别择”和“无感触”。在批判传统中国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借助于西方的思想理论武器,从明晰“历史之范围”出发,对“史学”进行了新“界说”。他认为,“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 (p2,11)运用西方进化史观,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即用国民史代替传统中国史学的政治精英史、皇朝史,最终揭示出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公理公例,这就是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 事实上,在发表《新史学》的前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就已经发表了试图改造中国史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国史叙论》共8节,除第一节“史之界说”外,其他7节所论述的都是编撰新型中国史所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和“时代之区分”。在“史之界说”中,梁启超提出了“近世史家”与“前者史家”之“本分”的不同,亦即“新史学”与传统中国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第二,“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3] (p1)在这里,梁启超已经
初步描绘出了“新史学”一些方向性的基本轮廓:在史学任务上,“新史学”把揭示历史因果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在史学方法上,“新史学”以动态的历史解释、分析而非静止的历史事实叙述和历史现象描述为主要方法;在历史观上,“新史学”将采用近世进步史观,抛弃“前者史家”的“兴亡隆替”的历史循环论;在历史内容上,“新史学”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即国民的历史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在发表《新史学》的同一年,梁启超又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可以看做是他把“新史学”观具体运用于历史实证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个案成果。在这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中,梁启超贯彻了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所提出的动态的历史解释和分析的方法与进步史观,并率先把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考察。梁启超根据学术思想的内容和历史演变的生命律,把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变迁划分为八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14](p3) 梁启超不仅试图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史学”的样式,而且也试图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创造一个“新史学”的模式。这首先表现在1902年他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和关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两部著作的发表。翌年,梁启超又发表了关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 此后,梁启超在中国史领域可以说进行了全方位的“新史学”尝试,并在世界史的许多领域做了“新史学”的探索。仅以学术思想史研究为例,梁启超不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经典作品,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孔子和墨子三大家做了详细的学案式的梳理和研究,校释了《墨经》;并对《庄子》、《韩非子》、《尸子》等诸子作品中有关学术思想史的篇做了释义式的研究。 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口号,呼吁“史界革命”,当然并不只是要在历史学的一些个别领域进行小打小闹,只在历史学的一些微观和中观层次进行零星的“革命”。他的最终目标是要为世人奉献出一部贯彻其“新史学”思想、体现其“新史学”精神的《中国通史》和《世界史》。从《饮冰室专集》的《残稿存目》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曾有撰著《世界史》、《国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科书》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其中有的已经写出了部分编章,如残存的《国史稿》第一编《上古史》和第三编《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稿共94页。但终其一生,梁启超并没有能够完成”新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通史》和
《世界史》两大通史的写作,其“新史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系列专门史领域。也许正是有鉴于梁启超“新史学”努力虽不能言失败但实未获圆满成功的经验教训,后来的唯物史观派历史学家们便把精力主要集中在通史的撰著方面,把唯物史观首先贯彻于通史之中,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专门史研究与其他“新史学”学派相比严重滞后,其成果与他们的相应成果相比实逊色良多;而且,这些通史成果,今天从学理的角度看,都存在着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端。 中国“新史学”开山人物梁启超的“新史学”实践表明,企图为新史学在各个方面都描画出一幅清晰的图样是徒劳的。在推进史学的发展上,新史学至多只是为历史学者提供一个为之努力的方向、一条为之前进的道路和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 新史学,犹如一位美丽的梦中“淑女”,可以意会却不能相及——果真及之,“淑女”则成“昨日黄花”。然而,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正是新史学这位“窈窕淑女”,令历史学者们为之心醉,沸腾着历史学者的血液,令历史学者孜孜不倦地“寤寐求之”,并为之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毕生的精力;亦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不断探求中,历史学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