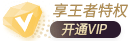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第五编、从生产到再生产:晚年思想1.从《资本论》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2a.从物质生产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2b.亲属关系结构的意义...........................................2c.家庭与氏族的关系.............................................4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3.东方社会研究.......................................20a.俄国农村公社研究............................................20b.跨越“卡夫丁”峡谷..........................................25第五编、从生产到再生产:晚年思想1.从《资本论》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a.从物质生产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b.亲属关系结构的意义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①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摩尔根把家庭形式分为以下各种(第27、28页):(1)血缘家庭;兄弟和姊妹群婚;马来亚式亲属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的(而且现在已成了这种家庭存在的证据)。(2)普那路亚家庭;这个名称来自夏威夷的普那路亚亲属关系。它是以几个兄弟和他们彼此的妻子的群婚或几个姊妹和她们彼此的丈夫的群婚为基础的。这里所用的“兄弟”一词,包括从(表)兄弟、再从(表)兄弟、三从(表)兄弟以及更远的从(表)兄弟,他们彼此都互认为兄弟;“姊妹”一词则包括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三从(表)姊妹以及更远的从(表)姊妹,她们彼此都互认为姊妹。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的亲属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的。这两种家庭形式都属于蒙昧期。(3)对偶制家庭;来源于σδáω一词,意为配成对[(σδà——意为成双。欧里庇得斯)。被动语态:被配成对或被结合在一起;柏拉图,普卢塔克],[σδασμó——配成对。普卢塔克]。这种家庭的基础是一男一女结成配偶,但并不是独占的同居;它是专偶制家庭的萌芽。丈夫和妻子双方都可随意离婚或分居。这种家庭形式并没有创造出特殊的亲属制度。(4)父权制家庭;以一男数女的婚姻为基础。在希伯来人的牧畜部落中,酋长和显要人物都实行多偶制。这一制度没有普遍流行,所以对人类的影响不大。(5)专偶制家庭;一男和一女实行独占同居的婚姻;它主要是文明社会的家庭,本质上是现代的东西。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亲属制度。(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36-337页)随着专偶制婚姻的产生,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亲属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旁系的亲属关系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希腊和拉丁部落在有史时期之初的亲属制度。(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37-538页)这种亲属制度和古老形式的氏族组织,通常是一起被发现的。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53-354页)c.家庭与氏族的关系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迄今为止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编纂学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作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以下一个荒诞的,尤其在18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发的: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围绕它而逐渐萌发起来的核心。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和十分受人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假想的男始祖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genneNtes)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亲属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同胞族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划分成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起初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族系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我们只是偶而听到这种族系,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奇怪,格罗特先生!),有一个共同的超人的男始祖和族系,像比较有名的氏族那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直白地说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族系,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族系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种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经十分久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接纳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①和尼布尔所作的那样,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从而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氏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6-117页))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0页)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发挥出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摩尔根说:“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胳的骨片,来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页)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还能表明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比如,据格罗特说:“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男始祖。”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作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69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自然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朗日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法庭和行政机关。70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干涉自然形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VoK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oK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buleN),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71。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对当时局势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扔出去让狗吃掉。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2.人民大会(agora[阿哥腊])。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代》),“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办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3.军事首长(Basileus[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共和党人美国佬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油滑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在他们那里似乎有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而且规定得很充分但是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看来,格莱斯顿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也已经充分地等于没有,尽管并不是明确到了极点地等于没有。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半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继承的。出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男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屏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那里,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因此,这种推想说明,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指挥是不好的,应该由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69“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既不让亚加米农也不让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而是让‘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等人,也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可见,用KoKnig来翻译Basileus一词,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oKnig(Kuning)是由Kuni、KuKnne而来的,即氏族酋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basileus跟现代意义的KoKnig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leia很确定地叫作patrikeN,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77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basileia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78;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来的意义上的统治权力。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旅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的[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即贵族、Geomoren即农民和Demiurgen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①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专偶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面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议事会规定由400人组成,每一部落为100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这里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薪饷。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公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其后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即所谓德莫,分别实行自治。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30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庙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侍奉他们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实行自治的美洲市镇区的一种原型。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借以开始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借以完结的单位相同。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将军,统率在部落境内征召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5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公事;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所以18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pllicées)。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LandjaKger。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工作。这仍是旧的氏族观念。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82,——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16-123页)3.东方社会研究a.俄国农村公社研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论据如下: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总之,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编者注]。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注:路·摩尔根。——编者注](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inasuperiorform)的复活(arevival)”。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显然是死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末,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的时代,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tribusdescon-fédérations]之间已经每年重分土地,但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由此可见,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