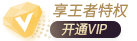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书写(新1)“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章清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不易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对中国的意义自然不可低估。*本文是作者参与德国学术基金会(DAAD)资助项目“ExchangesofKnowledgebetweenChinaandtheWest:HistoricalandPhilosophicalDimensions”完成的部分成果,曾蒙Prof.MichaelLack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