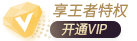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
——在日文写作中
计璧瑞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10年09期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集刊》(厦门)2010年1期第18,26页
【英文标题】On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Colonial Taiwanese Literature Written in Japanese
【作者简介】计壁瑞,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要】本文探讨日文写作在殖民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文化想象的变异。在中文写作的对照下,日文写作经历了文学主角由悲苦的 民众转变为内心焦虑的知识分子、传统从被批判的对象过渡到民族的身份标记而被肯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迫隐退、“日本想象”转向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等变化;民族自我想象有时会通过“日本想象”得以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也随着殖民社会的演进呈现不同的状态。 The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on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al imagination about colonial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Japanese. These works in Japanese had some Changes, such as major characters were from miserable people to anxious intellectuals, cultural tradition was from a criticized object to an affirmative national symbol, etc. There was different soul pain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with evolution of colonial society.
【关 键 词】文化想象/日文写作cultural imagination/written in JapaneseEE411UU1647979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0)01-0018-09
自20世纪30年代后,日文写作逐渐成为台湾新文学的主要写作形态,至1937年后更成为唯一的写作形态。从语言使用上看,这种转折似乎是断裂式的,但事实上文学整体而不是单个作家的写作断裂并没有发生。不用说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存,就是文化想象方面也存在中日文写作的自然衔接。在语言转换的当下,文化想象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或者说,此刻想象的变化主要不是受语言转换的影响,更多地是受制于社会思潮的变迁,与中文写作进程中受社会影响发生的变化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日文写作仍然在想象领域的拓展、想象方式的多元等方面显示了与中文写作的差异,特别是将日文写作后期的文本与中文写作初期的文本相比较时,差异就更加明显。如果把殖民地台湾新文学视作一个整体,把主要以中文写作为基本形态的时期、中日文并存的时期、日文写作时期依次串联起来,文化想象的渐变脉络是相当清晰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1937年,可谓中日文写作并存的时期,?日文写作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杨逵、吕赫若、翁闹、巫永福等开始登上文学舞台。从一开始,日文写作似乎就不存在中文写作文化想象上的共同指向,文化立场和关注焦点也因人而异,甚至因同一位作家的不同文本而异,没有明显的群体化特征。杨逵、吕赫若的写作更多地承续了中文写作一以贯之的反映社会问题、关注民众疾苦的精神;?翁闹、巫永福等人的写作时代表征相对淡化,殖民社会矛盾冲突的紧张感并不强烈,更多的时候以描摹人的生存状态或内心活动见长;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重要作家龙瑛宗和张文环,在复杂严苛的文化环境中以出色的艺术想象力展示了创作主体的内心焦虑和对台湾风物的精细描绘。文学与切近的现实问题的距离普遍加大,作家的个性化和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因此以某些共同特征来说明日文写作是比较困难的。从与中文写作的比较中观察日文写作文化想象的变化可能是较为便利的立足点。
一
悲苦的民众形象仍然是日文写作民族自我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可能不再像中文写作中那样地位突出。深受左翼文化运动乃至工农运动影响?的作家仍然致力于表现激烈社会冲突中民众的受难者形象,但想象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然主义的痕迹减弱,民众的觉醒意识增强。这种变化的主要体现者是杨逵,他的《送报夫》呈现了殖民暴力下农民丧失土地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但人们还是竭尽全力做出了最后的抵抗。在日本目睹了阶级压迫,获得了被剥削阶级同情的主人公认识到阶级对立可能超越民族冲突:“在家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一直都恨着他们”,但到了东京却发现“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一样,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小说文化想象的重要突破在于通过空间的转变扩展了殖民社会阶级冲突的认知,将阶级而不是单纯的民族当做划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基本尺度,使本民族被压迫者与异民族被压迫者站到了一起,为社会问题的想象注入了新的因素。?《顽童伐鬼记》中日本青年、平民美术家健作发现下层民众的子弟,不管是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都只能在垃圾场玩耍,相邻的优美庭院却被工厂老板所占据,于是他和孩子们一起为争取游乐空间而行动,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美术’”。其中超越民族的阶级意识同样明显。作家明确的政治观和文学观对写作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也有《无医村》里绝望无助的人物,但杨逵的大多数小说人物具有昂扬乐观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意志,改变了中文写作中黯淡压抑的氛围和底层民众的屈辱处境。
与中文写作描绘悲苦民众形象几乎完全一致的是吕赫若的《牛车》。交通的便利、汽车的通行逐渐使牛车运输失去了生存可能,以赶牛车为生的杨添丁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辛勤,却依然陷入绝境。他无法解释生存的悖论,而把汽车当做苦难产生的原因。他推倒了阻碍牛车在道路中心行走的路碑,却推不倒强大的殖民暴力和经济压迫。杨添丁是不觉悟的,与此前中文写作中的众多受难兄弟一样;但年仅21岁、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者吕赫若却已明确揭示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封建自然经济的剧烈冲击,它虽然能为资产者的财富积累创造极大的便利,却给无产者的生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明的发展以牺牲底层民众为代价,同时又是在殖民社会中实现的。《牛车》的文化想象于是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殖民资本主义本质,即兼具资本主义掠夺和殖民社会暴力双重性的揭示,一是从经济领域再次透露出传统与现代、旧与新、道义与霸权的对立。农民们依据的经验意识到“在日本朝代里,清朝时代的东西都不中用了”,进而“以为文明的利器都是日本特有的东西”。他们所代表的
传统虽然具有道义的优势,却依然不得不在与先进霸权的悲剧性对抗中步步退让。这正是《牛车》超越以往对社会问题和民众疾苦的自然主义式想象之所在。杨逵、吕赫若的出现联系着中日文写作关怀下层民众的共同主题,没有他们的努力,中日文写作文化想象间的差异会加大,文化想象的平缓过渡会受到影响。
关于传统,日文写作显示了比中文写作更加浓厚的想象欲望,而且态度相对平和,吕赫若、张文环等重要作家更是以民俗风情描绘见长。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既可能仍然以其落后性而继续成为批判的焦点,又可能出于作家对民族精神的追寻而化作客观的审美对象。这个时期,殖民文化的渗透力大大增强,新文学与传统的紧张关系相比于社会运动最为激烈的时期有所缓和,作家对待传统的心态也有所改变,传统在文化想象中维系民族身份的作用得到加强。日文写作想象传统过程中知识分子式的矛盾困惑相当明显,但与赖和式的想象略有不同。赖和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心境更多地带有社会政治层面的焦虑,日文写作则侧重于文化问题,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探讨,直接的政治问题既不为时局所接受,也不为绝大多数日文作家所擅长。由于日文作家通过日本较多地触及到现代文明观念和形态,自身与传统的关系相对不十分密切,因此想象传统也具有相对冷静旁观和将传统审美对象化的特点。
对传统落后性的批判仍然是以现代观照传统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虽然日文写作的批判锋芒相对平和含蓄,传统往往像一个悠长的故事,与想象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也因此在现代人近乎于追忆的描摹中,浮现出它本来的保守和丑陋。毫无疑问,婚姻家庭关系是这个悠长故事的重要情节之一。吕赫若《庙庭》和《月夜》这两篇情节连续的小说讲述了女子翠竹丧夫再嫁,受到婆家百般凌辱被迫投水自尽的故事。传统对女子再嫁的歧视、男性玩弄女性的恶行、姑婆的刁蛮、娘家的软弱,一起将翠竹逼上绝路。这是两篇典型的表现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处境的小说,其情节和人物命运呈现出人们所熟知的惯常模式,但另一人物“我”的出现却以近于旁观者的姿态打破了惯常的客观叙述,增加了另一种文化力量与传统的交锋,引申出了新的想象内涵。归乡的“我”受舅父的委托将无法忍受虐待跑回娘家的表妹翠竹送回婆家,这个软弱、犹豫不决、毫无行动能力的人物在同情翠竹的痛苦和顺从传统的意志之间承受着内心的折磨,然而“我”还是选择了妥协,带着内心的不安期待奇迹出现,但翠竹的投水使“我”的期待彻底幻灭。“我”的尴尬流露出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遭遇现实中的传统时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离乡多年的“我”对传统的想象只是儿时香火繁盛的关帝庙和与翠竹嬉戏的诗意场景,现实的传统却露出了无情的“吃人”本色。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极度不适应其实也流露出传统向现代过渡中知识分子必然的情感反应。这使小说在寻常的故事模式之外提供了展现知识分子式传统想象的机会。
将传统的崩坏寓于对习俗风土人性的精细描摹,是张文环《阉鸡》、吕赫若《风水》、《合家平安》等小说审视传统的独特方式。那只古老的木雕阉鸡仿佛是封闭保守的乡村和旧式家庭丧失活力的标记,那些身体的和精神的残缺者们失去了创造生命的能力和渴望,逐渐趋于灵魂的死灭,青年女子月里鲜活的生命几经挣扎终于被黑暗所吞噬。在极度精细客观的描绘中,张文环不动声色地将停滞的封建社会扭曲、扼杀人性的残忍表露无遗,于乡土风情书写的背后透露传统社会的没落。作者的另一篇小说《论语与鸡》嘲讽了乡人的愚昧迷信和教书先生的斯文扫地,在“山里的小村子,也在高喊日本文明”的时代,传统无可奈何地成为笑柄。《风水》自然也与传统有关,周长乾周长坤兄弟二人在对故去父母尽孝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周长乾遵从习俗以尽孝道,周长坤对风水的理解则完全与是否能庇护自己相关。贪欲与私利战胜了淳朴和善良,风水依旧,但人心不古。《合家平安》描写封建旧式家庭的寄生生活因吸鸦片而彻底败落,稍有转机后又故态复萌,一群失去了生命力的人物喜剧性地走向消亡,宣告了传统中孳生的堕落的人性已不再有存在的价值。在张文环、吕赫若的笔下,想象传统开始从表现社会问题的立场转向探索人性的立场,并不特别强调传统的丑陋与社会苦难的紧密联系,即不注重从制度的角度寻找社会问题的原因,而注重人性的因素,在人性的泯灭中奏响封建传统的挽歌。但注重以表现人性来表现传统也显现了作家想象传统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即一方面感知传统的荒谬落伍,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将人性的堕落视作传统崩坏的原因,而对传统本身的道德评价却不一定都是负面的。《风水》中的人物无论善良还是贪婪都对风水的存在深信不疑,作家的批判指向并不是风水习俗,而是人的贪欲。当善良的人性与习俗风水相联系时,后者反而成了评价人性的尺度;特别是不尽孝道、破坏风水的周长坤因儿子学西医而家道显赫,似乎也暗示着人性的贪欲与现代文明的侵蚀有关。孝道曾在吕赫若的多篇小说中出现,而且不是作为传统的负面因素。显然,某些传统观念和具体生活形态在作家的传统想象中得到了肯定,这表明日文写作中传统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完全意义上的批判对象转变为既被批判又在特定情况下获得了某种认同的文化对象,昭示着日文写作民族自我想象的复杂心态。这些作品“在批判传统台湾家庭中的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带有记录、保存在皇民化运动中逐渐消失的传统家庭关系与台湾文化的意图”。?从表面上看,作家社会批判的锋芒有所减弱,而人性探讨却相当深入。
在这样的想象基础之上,日文写作就不单只有在传统社会中被压抑被损害的人物,也诞生了明朗、健康的形象。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形象的出现是因对传统正面意义的肯定所致,但在传统氛围中发掘健康的人性,仍然表明民族自我想象中积极因素的出现。吕赫若《山川草木》塑造了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能够主宰土地和个人命运的青年女性宝连的形象。这个在东京学习音乐的现代女性,当家庭变故之际毅然放弃学业,带领弟妹回归田园,在故乡的山川草木间获得了崭新的生活。和宝连相比,张文环《夜猿》里的人物完全生活于静谧自然的传统社会,深山里独处的农家每日与大自然朝夕相伴,在风声竹吟猿鸣中舒展着生命的创造力。这两篇创作于殖民晚期的小说通过赞美自然人性来肯定民族自我,为殖民统治最为严密的时刻树立了台湾人的富有审美意义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文学在特定时局下逐渐被迫削弱了表现社会问题和社会批判的功能。从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到40年代,越靠近殖民末期,日文写作的社会批判意识越淡薄,自然和人性的色彩越突出;政治观念的张扬渐渐消退,艺术经营日臻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文作家在压力下彻底放弃了民族立场的坚持,20世纪40年代初张文环、吕赫若等人的《台湾文学》与以日人为主的《文艺台湾》的对抗就是台湾作家为争取生存空间、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作的努力。?虽然相当短暂,但正因为有这样的对抗存在,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说日文写作想象传统的复杂心态和乐观向上的人物形象营造其实是肯定民族自我的曲折方式。
二
日本想象这个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日文写作中相当引人注目,它不但承载了作家关于殖民社会矛盾的思考,而且深刻地传达了殖民时代台湾人浓重的文化身份焦虑,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被殖民者身份焦虑是由日文写作中的日本想象来完成的。较之中文写作,日文写作经历了殖民社会从文化对抗到对抗消隐的过渡,经历了殖民同化进一步加深、民族间激烈的政治文化冲突基本平息、原有民族身份标记被严重涂抹的时期。?因此,其日本想象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想象的前后变化比较明显;二是想象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强;三是日本想象常常与民族自我想象相融合,即在日本想象中想象台湾,日本开始成为某种参照,服务于台湾人的自我定位。总体上,日文写作中的日本不再像中文写作中那样作为绝对外在于台湾的异族统治者形象出现,而是随着对抗的消隐逐渐渗入台湾社会;它的异质性仍然保持着与台湾的对立,但它对台湾社会生活的影响激发了作家思考复杂的文化问题。在殖民后期,殖民者的思想、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都可能通过压制和渗透融入被殖民者的思维中,直接导致后者发生文化
身份认定的混乱;同时,在民族矛盾趋于隐蔽的时期,两种原本对立的意识形态或体现意识形态的具体生活形态可能会取得暂时的力量均衡进而平静相处,这才是问题复杂性之所在。
正像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日文写作并存时的日文写作承续了中文写作民族自我想象的主要特征一样,这个时期部分日文写作的日本想象也维系了中文写作对殖民者的一贯认识。颟顸、霸道的日本人形象继续在《送报夫》、《牛车》、《豚》等小说中出现,但随后这样的形象渐渐消失,?不再作为压迫者的日本人悄然出现在台湾人身边。这种迹象至少说明文学和作家开始接受日本人的非殖民者形象,属于绝对的殖民暴力的日本想象内涵发生了改变。到了20世纪40年代皇民化运动高潮期,作家无论是否受到左翼影响,其意识形态色彩都已隐去,在当局文学奉公、增产建设的所谓“国策”和口号的倡导下,杨逵、吕赫若等作家也在1944年前后受总督府情报课的委托到生产第一线,写出了《增产之背后》、《风头水尾》等作品,在名义上属于当时的“国策文学”。?从杨逵、吕赫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观和创作以及战后的意识形态来看,本时期的如此举动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妥协,特别是这两篇作品并不涉及对“国策”的颂扬,只是以努力工作着的台湾人形象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度,传达了企盼台湾社会发展的愿望,而这与当时的政治号召是一致的。但作家配合“国策”的确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张文环也曾为
宣传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保健知识宣传1冬季预防流感知识宣传手足口病防知识宣传森林防火宣传内容
“志愿兵制度”写过文章。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思维去判断。这里提出几种理解,一是作品的内涵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作家有可能在时局的压力下被迫做出配合当局的举动;二是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同化,特别是战时当局物质和精神双重动员的台湾人,可能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妥协;三是当局推行的增产建设方针与台湾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在效果上有相近之处;四是文学本身的因素,文学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工具,当文学不再有机会表达思想倾向时,作家当然可能放弃文学的这一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发微探源、寻找作品的微言大义很可能是徒劳的。日文作家的上述“转向”既可能出于单一的因素,也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本想象的变化当然和这些因素有关。吕赫若写作《玉兰花》(1943)和《邻居》(1942)的时候,其意识形态表达已经不同于《牛车》时期,(11)无论从他本人的写作还是殖民地台湾文学而论,这两篇小说都意味着新的日本人形象的出现。《邻居》中一对心地善良的日本人夫妇与台湾人比邻而居,因不能生育而领养了台湾小孩,并百般疼爱。他们平等地与台湾人生活在一起且怀有深深的爱心,这完全超出了主人公“我”对日本人的固有印象,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本来不应如此。时代的“大叙述”已完全被具体的、个人化的生活形态所取代,似乎表明作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日本作为绝对的“恶”的化身,而渐渐地接受日本这个“大概念”包容的一部分正面形态,注意到了民族矛盾的大前提下还有着人性的共通之处。(12)但这种原有想象的打破反过来印证了原本存在的民族间的隔阂和原有想象的存在。《玉兰花》的情形比较特别。在一个儿童的眼中,铃木善兵卫是被“不停地将新时代的空气引入家庭”的叔父从东京带来的、携着照相机的日本人。起初他被当做怪物,因为“每当我们哭泣不止时,祖母或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看~日本人来了~’为的是阻止我们哭泣。由于从小被恐吓,我们对日本人因而非常畏惧”。然而渐渐地孩子开始走近铃木,感受到他“充满喜悦、爱的善良的眼光”,产生了依恋的感情。多年后铃木的照相机留下的照片还在唤醒孩子成人后温馨的回忆。表面上非常符合当时所谓“日中亲善”的主旨和人性主题的《玉兰花》,深层的意蕴直接与作家对中日关系的再度想象有关。它富于暗示性地延续了台湾,日本、传统,现代的矛盾想象——带着孩子们从未见过的、象征现代科技文明的照相机,从现代化的日本来到传统的台湾乡间的铃木散发的迷人的吸引力暗示着现代日本对传统台湾的巨大感召,而这一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不再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这意味着作家在再度想象中做出了新的取舍:在民族矛盾隐晦之际专注于现代性的追求。孩子对铃木从惧怕到依恋的过程也在说明台湾人,至少是知识分子对日本从完全排拒到既排拒其殖民性又接近其现代性的认知转移。
当写作服务于明确的反帝、反封建主题和表现人民苦难的目标时,关注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势在必然,伴随殖民压迫而来的现代文明常常激发作家充满矛盾的联想,毕竟日本呈现的现代性与对被殖民者的压迫掠夺相伴而生;当写作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或社会矛盾暂时隐去时,日本又以较为单纯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姿态出现在台湾人面前。日文写作这一点尤为突出。较早出现的,追风所作日文小说《她要往何处去》(1923)中的日本即以开放、自由、文明的形象成为年轻人寻求个性解放的梦的国度,那艘载着希望和梦想的海轮来了又去,连接着彼岸的浪漫故事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桂花从海轮上收获了自己破碎的梦想,又乘海轮奔赴“内地”(日本)去编织新的梦境。与古老传统的台湾相比,日本分明是“姊妹们”摆脱苦恼的新生之地。这篇小说由于未涉及民族冲突而提供了单纯明朗的日本想象,但其产生仍与《玉兰花》不同,前者表现的是台湾知识分子最初接触象征现代文明的日本后的单纯的向往,后者是在历经民族冲突和左翼运动洗礼以及殖民统治晚期的社会压力后,对传统,现代关系的再度思考。
但殖民社会的压力并未被忘记。那些表现深刻或潜在殖民社会文化矛盾和身份焦虑的写作开拓了日文写作又一方想象天地。(13)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1937)在日本人和台湾人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外在形态下描绘了台湾人不同的心态,记录了小知识分子陈有三由满怀希望到沉沦绝望的历程,无论他怎样挣扎,台湾人身份都是抹不掉的印记,时时引发他心中的隐痛。他确切地知道“我是谁”,却不得不在清醒中忍受痛苦。而那些曾经留学日本、接受打着深深的日本文化烙印的现代文明、已无法清除思想文化结构中日本因素的人物,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认却显得十分迷茫。这些“走出去的人”似乎更能说明身份失落的困境。其中王昶雄的《奔流》在这方面相当突出。
《奔流》发表于1943年,此时,完全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一代台湾人已经成长起来,“走出去的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异国文化经验,开始真正面对两种文化冲突导致的内心焦虑,弱势的故土文化和强势的日本文化交织而成的不和谐身份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究竟做日本人还是做台湾人,抑或先做台湾人再做日本人,这些问题在他们心中萦绕多时却鲜有明确的答案。
小说的三位主要人物是两位“走出去的人”——“我”和伊东春生,以及即将走出去的林柏年。当“我”“离开住了十年,已经习惯了的东京”,子承父业回故乡做乡村医生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困惑:“数年没见的故乡风物,真正打心底里感到优美,心情是很开朗的。但不能持久。”乡村的单调刻板使“我”“很想干脆抛弃一切,再一次回到东京去”,“并不是自动地努力于内地化,而是在无意识中,内地人的血,移注入自己的血管,在不知不觉间,已静静地在流动那样的心情”。潜移默化接受日本文化、曾经隐瞒自己台湾人身份的“我”,仍然有殖民地人民特有的敏感,“在内地的时候,内地人当然不用说,是本岛人还是中国人,看一眼,就能毫无例外地认出来”。困扰“我”的是生为台湾人的文化压力时常提醒自己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尽管“我”倾心于所谓“日本精神”。小说着力描绘的伊东春生,认同殖民现代性,以其昂扬、优越、讲日语、改日本姓名、娶日本太太,处处实践着“日本精神”,不但以做台湾人为耻,也以自己的台湾父母为耻;他想象中的台湾人胆怯、闭塞,“殖民地的劣根性经常低迷不散”,回到台湾并不能唤起他对故土亲情的眷恋。但他并不是滑稽剧中的丑角,毋宁说是作家严肃思考身份问题的对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否一定要鄙夷台湾,做台湾人是否一定意味着屈辱和卑下,小说用年轻的林柏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位纯真执著的青年不齿于伊东春生的行为,坚定地认为“我若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更非是堂堂的台湾人不可。不必为了
出生在南方,就鄙夷自己。沁入这里的生活,并不一定要鄙夷故乡的乡间土臭”。三位人物对自身文化主体性格的认知各不相同,但其行为思考的背后均隐含着“本岛青年两重生活的深刻苦恼”。
《奔流》是殖民时期少有的兼有知性思考和复杂内心冲突的作品之一,限于当时的局势,它对问题的解答仍然相对朦胧含混,一方面抒发热爱乡土的情感,一方面不得不把实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平等的理想放在做“堂堂的日本人”的理念下。日本不仅是那个优越、现代、居高临下的民族和国度,似乎还是台湾人维护尊严、提升自己所设定的抽象目标。林柏年终于到日本去了,不是为了背弃故土,而是要做真正“堂堂的台湾人”。
这里,日本想象和身份问题合而为一,作家在日本和台湾两大主体中探讨台湾人的归属。按照研究者的说法,“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一个人可以属于不只一个群体”,“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当一个人由追随一个群体而转向另一个时,他的身份看来会发生很多变化”。(14)虽然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成规”而使自己在不同的群体中保持不同的身份,但一种成规试图强制性地取消另一种成规,如皇民化运动对台湾人身份的取消,必将导致台湾人在“指认身份”和“自塑身份”之间做出调整,要么彻底改换身份,如伊东春生;要么在两种身份的纠结中苦苦思索,如“我”;要么为保持原有身份而决心赢得新的身份,如林柏年。由于日本、台湾两种文化力量的极度不对等,在中国传统的孝道外,林柏年几乎找不到建立主体的文化表征,维持其精神不坠的除了内心对故土的挚爱,竟是日本剑道勇敢不屈的精神。他对台湾的想象终于还是通过对日本的想象才得以实现。林柏年面临一个悖论:他试图通过赴日留学确立身份的过程注定是原有身份进一步丧失的过程。这时人们发现,被殖民者身份的重建其实已无法摆脱殖民者话语权力的控制。
无论传统,现代关系的审视还是身份焦虑,无疑都是由知识分子角色完成的。其中自然包括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作家持有的知识分子立场。迷茫、沮丧、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形象代表日文作家抒发着殖民时代晚期的苦闷和忧郁,知识分子式的精神痛苦的确是日文写作异常突出的想象特征。再来看《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初出校门的陈有三来到乡村小镇做职员,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和鄙俗的环境,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处境。然而复杂势利的人际关系、被殖民者低下的地位、周围人们的挣扎和苦难,一步步销蚀着他的精神和理想,使他被“绝望、空虚与黑暗层层包围得转不过身来”,无奈地滑向深渊。龙瑛宗创造的这个具有“零余者”精神特质的人物集中了个人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的总体氛围是灰暗颓废的,在陈有三周围,聚集着众多濒于毁灭的人物,唯一一位在绝望中仍努力思考的人物——林杏南长子,也以宿命的方式空洞地做着“切不可轻易陷入绝望或堕落”的劝慰,最终以死亡印证了思想的无力。所谓“宿命的受容”(15)概括了当时知识分子无力反抗、沉沦于孤独和虚无的精神苦难,昭示着与此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异。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在《台湾文学备忘录——台湾作家的三部作品》中比较《送报夫》、《牛车》与《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指出:“如果按照年代顺序读一下这3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台湾人作家的意识从抵抗到放弃,进而屈服这样一个倾斜的过程。”(16)也可以说,这篇小说从时间上开启了此后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为殖民社会晚期重要文化想象的过程,也与《奔流》、《清秋》等一起组成知识分子探索出路的几种不同方式:《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以绝望的挣扎显示“零余者”的毫无希望;(17)《奔流》通过不同人物类型表现不同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清秋》在内心的探索中追索生命的意义。在情绪上,从无奈的愤激和极度的精神痛苦到茫然中的思考和思考后的抉择,直至进入内心的形而上探寻,这三部小说从躁动走向沉郁,似乎也在说明知识分子随着殖民社会演进的情绪变化轨迹。
1944年吕赫若的《清秋》发表时,殖民统治已经到了终结的前夜。留日学成返乡的耀勋开始在都市文明、日本文化和乡村情致、中华传统间苦苦思考。这位应父祖的要求打算返乡做一名乡村医生的青年从回到家乡之日起,就开始了矛盾困惑的心路历程。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祖父,以及光宗耀祖、恪守孝道的观念深深吸引着他,传统读书人的学问文章在他心中比现代医学更有魅力。但作为曾在异域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耀勋仍难以抑止走出传统的欲望。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他这里转化成对生命本源的思索,因为在时空流转中他直接产生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茫然。耀勋没有像陈有三们那样因现实生存陷于困境而直接引发精神的幻灭,虽然他的思索并未脱离台湾社会的具体情境,但重心更多地放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因而带有相当明显的形而上色彩。在时局压力下作为以往想象的一种替代,耀勋这类既有深切社会关怀,又有终极精神追索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是作家想象重心转移后产生的新的想象内涵的一部分。这里人们再一次发现了文学与殖民社会现实矛盾逐渐加大的距离和向知识分子内心靠近的趋向。
结语
当文学的主角逐渐由悲苦的民众转变为内心焦虑的知识分子、当传统从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过渡到作为民族的身份标记而被肯定、当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表现因时局而被迫隐退、当日本想象由鲜明的民族立场的昭示转向复杂的传统现代关系的考察之时,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已经发生了平缓而深刻的变异。在中文写作的对照下,日文写作的这种变异更为突出。划分不同语言的写作是试图为想象的变异寻找某种立论的格局和支点,并不否认二者间的交叉融合;同时变异的确发生于不同语言的写作之间,因为写作语言变化的背后是殖民社会双方政治文化关系格局的变化及作家的知识结构、社会境遇、文学传承等多重因素的改变,这些因素又是想象改变的重要原因。
注释:
?虽然最初的日文写作与中文写作出现的时间极为接近,但真正成为重要的写作形态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这并不是说他们确实从中文写作中继承了某种主题或具体想象方式,而是说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他们的日文写作呈现出与中文写作关注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疾苦相一致的倾向。从战后学习中文的情形看,他们当时阅读白话文的能力有限,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吕赫若能够阅读古典白话小说。
?影响既有来自岛内的,也有来自日本的。由于绝大多数日文作家都曾留学日本,而当时赴日留学往往是家境较好的青年的选择,因而部分日文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对生疏。这也应是日文写作底层民众形象减少的一个原因。
?杨逵是日据台湾新文学作家中最为鲜明的阶级论者,赴日期间接触日本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返台后投身于激进的文化运动和农民组合运动,曾多次被捕。他“主张在文学中‘寻找呐喊’:不赞成文学走上‘自然主义的、仅仅是对黑暗的细密的描写’。文学应该‘寻求光明’、‘呼唤希望’”。见陈映真:《激越的青春》,《吕赫若作品研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301页。如此文学观和强烈的政治热情、不屈的斗争精神折射于小说中。体现为对苦难民众觉醒和反抗的书写。
?垂水千惠:《吕赫若文学中〈风头水尾〉的位置》,北京大学、日本大学主办“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学术会议”宣读,2001年11月,北京。文章还指出,当时“反封建、朝向近代化的摸索已逐渐与‘皇民化’同调,而归向传统反而成为抵抗‘皇民化’之手段”。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日文作家对传统的矛盾心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1939年底,由日本、台湾作家共同组成的“台湾文艺协会”成立,1940年1月发行《文艺台湾》杂志,由日本作家西川满任主编;1941年3月西川满另组“文艺台湾社”,独自编辑发行《文艺台湾》,刊物遵循浪漫、耽美的艺术至上主义,成为在台日本作家写作“外地文学”的园地,部分台湾作家如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周金波等也加入了这一文艺团体。1941年5月张文环等台湾作家脱离“台湾文艺协会”和《文艺台湾》,另组“启文社”,创办《台湾文学》,注重写实主义,客观上形成了与《文艺台湾》在作家群体、艺术主张等方面的对垒。张文环、吕赫若、吴新荣等为该刊的主要作家,另有少数日人作家参加。后杨云萍、龙瑛宗等台湾作家脱离《文艺台湾》,转为《台湾文学》撰稿。1944年《台湾文学》被迫终刊,与《文艺台湾》一起组合为由当局控制的“文学奉公会”发行的《台湾文艺》。叶石涛:《〈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见叶石涛:《走向台湾文学》,台北:自立晚报出版,1990年;又见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第二章,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87年。
?在中文写作中,作者的民族属性、作品的文字属性和内涵属性三方面是统一的,有鲜明的民族定位,而日文写作则出现了矛盾,作者民族属性和作品内涵属性属于被殖民者,作品的文字属性却属于殖民者。事实上,在殖民末期民族文化身份被模糊的情况下,日文写作前两种属性的民族定位也不再像中文写作那样清晰。
?杨逵1942年的《鹅妈妈出嫁》是少见的殖民晚期明确描写日本人负面形象的作品。
?这些小说由总督府情报课编为《台湾决战小说集》乾、坤两卷,台北: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1944年,1945年。
?这种作家及其创作前后矛盾的现象首先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没有具体材料说明其成因时,人们应该做的是承认事实。但在时间、政局、文化生态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当事人和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按照某种既定的、易于被接受的结论去重新构想事实或凸现某一部分事实。
(11)这个时期吕赫若不再显示明确的政治意识,他的日本友人认为“看不出他所持有的政治意识,是个带有小布尔乔亚洁癖的青年”,因而得以在“文学奉公会”主办的《台湾文艺》上发表作品。林瑞明:《吕赫若的“台湾家族史”与写实风格》,见《吕赫若作品研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3-74页。
(12)这不是说此前的日本人形象没有考虑其人性的一面是一种缺陷,而是说作家会出于想象的需要去确定他们想要表现的形象。吕赫若小说的不同以往的日本人形象当然是想象改变的结果。
(13)中文写作对身份问题也有零星的表现,朱点人的《脱颖》(1936)描写台湾青年陈三贵深知凭他台湾人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便挖空心思寻求机会,通过迎娶日本上司的女儿改姓“犬养”,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但陈三贵只是利用身份转换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并未历经精神痛苦;小说主旨也在讽刺少数台湾人趋炎附势、贪图富贵。因中文写作时期写作重心在于民族和阶级矛盾的外在表现,身份问题的思考并不突出。
(14)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121页。
(15)罗成纯:《龙瑛宗研究》,见《台湾作家全集?龙瑛宗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第241页。
(16)尾崎秀树:《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間ふさ子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第239-240页。
(17)导致不同探索方式的原因很多,龙瑛宗小说浓重的绝望、颓废情调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气质有关。NU26